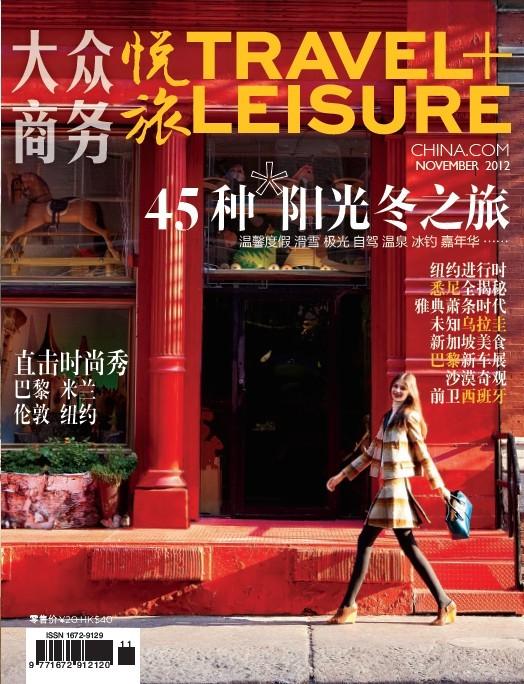一位70后的平面设计路

我是70年代出生的,一出生就面对社会竞争的各种压力。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,我们这代“70后”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,就是刻苦学习,考上大学。当年大学录取率非常低,大学生毕业后国家“包分配”进各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,这一生算是“保了险了”,所以家家父母都期望孩子能考上大学。对孩子来说,这是巨大的压力,我自己就考了两年才考上。
当年就读的“浙江美院”(现为中国美术学院),仅报名就有七千名学生,录取五十人。绝对得有“买六合彩的幸运”才行。我见过许多才华横溢的考生,五年、十年地耗下去,最后消失了。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,今天还有谁会记起他们?他们是不是也认命于时代悲剧呢?我希望有社会学者能写写当年的考生。
入学前我学了六年书法,临的是柳公权柳体。浙美当时的书法专业,隶属国画系,每两年才招生一次,每次招生四名。我想我不会成功,就转学平面设计的一些基础课程,觉得自己突然的离开虽然是“墨分五色”,但是从单一黑色的世界,进入彩色的世界,心情愉悦极了。
对了,当时还没有平面设计“Graphic Design”这个词,这个说法直到上世界90年代初,才刚进入中国,我们那个专业被称为“工艺美术系”。我入学那年一个班只有十二个人,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,与年龄最大的相差十一岁。
四年浙美的大学教育,把我从无知带到艺术和设计的入海口,毕业后的我其实一头雾水,面对着那片汪洋大海。当时已经在柏林留学的林家阳老师,他对我提供了出国留学和专业信息的实际帮助。我后来去德国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读的是历史系,文化史专业。课题是19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的东西海报艺术比较研究。去读这个文科大学的博士学位,是人生中的一个大决定。因为这个大跨度的改专业学习,在几乎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任何空闲时间。我在设计工作时感触到,平面设计需要多学科的知识,我抱着补课的心态,开始这个研究课题。
今天,平面设计师在不少场合抱怨,这个社会对设计师的地位不够重视,不够尊重。我觉得很多设计师其实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,尊重不是单方面可以被给予。不少设计师被出钱的雇主——甲方所引导,慢慢地培养习惯性的思维,“一切客户至上”。设计浪费、设计过度的现象泛滥。更糟糕的,有时还渐渐忘记自己的正义感,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这些经历让我形成对于“好设计”的看法,它应该“Originality, Revolutionary, Timeless”三位一体的概念。“Originality”,指的是设计思想和表现的原创;“Revolutionary”讲的是勇气,对历史、对理论、对经典、对先人成就的肯定基础上,不要习惯于墨守成规,不要“被思考”,要有“破”的勇气——“不破不立”。“Timeless”是审美带来的力量,审美会令这个设计作品突破了时空的界限。我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对平面设计师职业担当的看法,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,还有比如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・哈特菲尔德(John Heartfield)用拼贴当时报纸的方式嘲讽纳粹的统治。一个社会应该多元,平面设计也应该如此,不论多少,总应有为穷人的设计,为弱者的设计。
订阅全年漫旅Travel+Leisure
-

- 《漫旅Travel+Leisure》杂志,旅行行业的风向标,最具魅力旅行生活的倡导者、报道者和分享者,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报道独一无二的旅行线路和享受之旅,真实的现场报道。